渎职侵权犯罪黑数的文化解读
“躲猫猫”是今年的一大网络热词,“今天你躲猫猫了吗?”成为众多网民的问候语。但这个熟悉的词语却有我们不熟悉的沉重词义。24岁的云南男青年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2009年2月8日在看守所内受伤被送往医院,2月12日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当地警方称其受伤原因是放风时和狱友玩“躲猫猫”撞在墙上。某网站2月14日即对“躲猫猫”词条进行了修改,添加了“娱乐性很强,在特定的地方进行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活动(监狱中、劳教所中或者看守所)”的释义,“躲猫猫”事件引发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十个官员九个贪,还有一个是脑瘫”的舆论背景下,不明真相的民众难免要猜测是否所有事故背后都有渎职犯罪,是否所有受贿背后都有渎职犯罪?在群众想象中,渎职侵权犯罪的数字被官方缩小了;而理性地站在法律立场,渎职侵权犯罪的数字却是被传媒和民众的想象放大了。
已经查处、正在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是否只是冰山一角?要说明这个问题,似乎只能靠数字来说话。但是,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渎职侵权犯罪像其他犯罪一样,必然存在犯罪黑数。所谓犯罪黑数,是指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被官方统计录入的犯罪数量。德国犯罪学家施耐德把犯罪黑数分为绝对黑数、半黑数和犯罪生涯黑数。绝对黑数是指实际已经发生,但并不为官方所掌握的犯罪;半黑数是指那些案犯未被抓获或未能将案犯定罪的犯罪行为;犯罪生涯黑数是指超出刑侦机关所发现和所能证明的、被判罪的犯人实际所犯的罪行【1】。
犯罪黑数的本质决定了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犯罪黑数研究都不可能毫不失真地澄清事实。但是,对于犯罪黑数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对于实现侦办渎职侵权犯罪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有现实意义的,而文化背景是犯罪研究,包括犯罪黑数研究无从回避的根本问题。
一、媒体的魔力:数字神话与沉默螺旋
在现代文明国家,媒体已经成为“第四权力”,以传媒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舆论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强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闻控制的本质是通过信息控制来控制社会意志与价值观念。当今社会,关于犯罪问题的报道,已成为大众媒介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对其所传播的关于犯罪信息的塑造决定着人们对于犯罪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这种影响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广泛、深远得多。
数字是最简单、最有力、最普遍的说明,大众相信数字会说话,但过分重视数据,而不去探求数字背后的真义,这样的数字根本没有实质的代表意义,只是一种盲目的数字迷失。信息时代,媒体迎合受众兴趣,受众关注引发媒体追踪,滚雪球的报道和舆论中看似最理性的数字可能是没有根基的。数字不会欺骗人,但玩弄数字的人却可能欺骗人。媒体刻意换算,利用数字来解释社会现象,意图达到预期的特定效果,早已成为大众习惯的模式。在我国,涉及下岗职工利益、地方经济发展或者党政机关领导的腐败问题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在大众的关注中,有些犯罪被人为放大异化了,这些犯罪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
从黄松有案到“躲猫猫”事件的舆论,不难发现传媒和公众的意见都是一边倒地对司法公正和国家公务员廉洁的普遍质疑。这固然受到“沉默螺旋”的控制,在舆论场域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会选择沉默以避免被孤立,如此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直到弱势一方在传媒舆论中失去或者说“放弃”发言权。由于“沉默螺旋”效应的作用,民意表达不是多数决定少数,而是少数意见领袖支配多数。当负面舆论产生之后,少数的意见领袖总是能够通过煽动性的言论将舆论往极端的方向推进。而对于公众而言,从众心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煽动性的一边倒的言论。这样,负面舆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不断积聚,关于事件的舆论就因此而被定格。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渎职侵权犯罪媒体泡沫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不正常态度。受众在接收媒体传达的信息之前其实已经存在“期待视野”,受众带着这种期待接收信息。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事件会被作为新闻加以报道,哪些被置之不理,绝不是一个随意的个人过程,编辑和记者们会按照一系列的专业标准确定一个事件的“新闻价值”而选择、制作和提供该新闻产品。被害人、犯罪分子和侦查人员被塑造成什么形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商业化的媒体运作(包括网络)必然受到利益驱动,而这时对职务犯罪的片面强化最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因为受众期待看到犯罪和背德。在制造新闻的过程中,一系列的新闻标准影响着涉及犯罪、违法及其惩罚的事件的选择和报道。这些标准使我们关注那些给公众提供理解犯罪信息时隐含的偏见。
近年来,网络民意已经成了一种能够对突发性事件做出强有力反应的有形实在,网络成了民意表达最汹涌的场所。2007年6月,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人,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网络民意的优势无须赘言,比如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多元化,意见表达的自由性和真实性,舆论传播的迅捷性和高效性。但另一方面,网络舆论也有先天不足。首先,我国网络舆论的代表性不高,从职业和行业分布看,多数网民属于中间阶层,现实社会中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中上网的人数比例很低,而且网民分布东西部差异也很大;其次,网民呈低龄化态势,青少年网民利用互联网的娱乐功能超过信息渠道功能等其他功能,网络舆论的可靠性较差;再次,网络的匿名性等性质影响了网络作用的发挥。
由于网络舆论中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缺乏直接表达的经济和技术能力,这些群体往往由“代言人”——同情或具有利益相关性的中间阶层网民——表达意见,而中间阶层网民不成熟的特点有可能使意见失真甚至严重扭曲。这样一来,占据网络舆论主体地位的很可能是中间阶层,现实社会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阶层,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等阶层群体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参与网络意见表达,这就使网络舆论对政策制定的作用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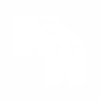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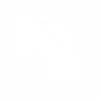
 咨询热线:18818883232
咨询热线:18818883232  QQ:1191193336
QQ:1191193336